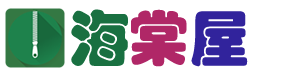第247章 泼天收穫,西门府眾女起风波
武松那头堪堪到,而史文恭带著王三官和一併团练子弟,路上扫了几个小寨子耽误了些时间,还在朝著曾头市赶去。
游家庄。
大官人愣著看著抱著她手的赵福金冷笑:“既是如此,你还不翻身?”
赵福金咬著那水灩灩的下唇,翻过那副高烧未退、软绵绵的身子,艰难地支起上半截。
她眼波横流,衝著大官人丟了个又嗔又媚的眼风,那病中的风情,竟比平素更勾人魂魄。
白腻腻软糯糯嫩嘟嘟。
自己唇上被咬破的伤口火辣辣地疼,手上鞭痕也针扎似的作痛,那点子怜香惜玉的心思,早被这痛楚和怒火烧成了灰烬!
一巴掌重重的拍了下去。
而此时西门府上晚上也是起了一场小风波。
这几日。
被罚做杂役丫鬟的金莲儿总算把今日的事情做周全了。她倚在杂役房那油浸浸的门框上,只觉腰眼儿酸,脊梁骨也似折了一般,也腻得人脑仁儿发昏,可心里却甜的发腻。
哼!
自己亲爹爹最后离去那一晚可是自己陪著的,身上都是自己的味儿。
抬眼望去,窗外月色早如凉水也似,泼银般泻了满院子,照在薄雪上。
金莲儿心头猛地一记:哎呀,香菱那小蹄子!今日大娘分派她去打扫书房这辰光了,不知道可曾拾掇乾净?还是去帮帮她!
念及此,金莲儿强挣起精神,挪动酸软的腿脚,穿廊过院,一逕往书房摸去o
书房门虚掩著,她拿指尖儿轻轻一推,吱呀一声开了缝。只见里面灯火通明,亮堂堂如同白昼。
窗欞子擦得鋥亮,书案上纤尘不染,连那博古架上几个玉摆件儿,都抹得油光水滑,映著烛火直晃眼。
她不禁暗忖:这香菱手脚倒麻利得紧!只是————人呢?
金莲儿心头疑云顿起,四下里张望寻觅。
循著声响紧赶几步,只见井台周遭积雪未消,月光惨惨白白地铺了一地,映得那水桶边沿寒光瘮人。
一个瘦伶仃的身影正佝僂在井台边,腰身弯得像张弓,死命地搓揉著手里物件。
口中呼出的白气一团团,刚离了唇便消散在寒气里。
想是冻得实在熬不住了,那小人儿猛地从冰碴子水里抽出一双红肿的小手儿,凑到嘴边,哆嗦著呵了几口热气。
金莲儿几步抢到井沿,低头细瞧—一老天爷!
那泡在刺骨冰水里揉搓的,可不正是书房里那张体面的墨绿绒面坐褥!
再看旁边地上,各色坐褥、椅垫、窗纱幔帐胡乱堆成了小山,全是书房並大厅上使唤的精细物件!
“香菱!”金莲儿心头一股无名火“腾”地窜起,劈手就攥住了那双还滴著冰水、肿得发亮的小手,触手只觉像捏住了两块冻透的石头,“你这个作死的小蹄子!冻掉爪子当柴烧么?这等醃攒粗笨的营生,自有浆洗房那起子粗夯婆子料理!你洗它作甚?大娘明明只叫你打扫浮尘、归置归置,几时叫你洗这些劳什子了?你是嫌命长,还是骨头贱?”
香菱被金莲儿这猛不丁一抓,唬得浑身一哆嗦,抬起脸来。
月光下小脸有些疲惫的笑道:“金莲姐,我、我原也是这般分说的,可那些浆洗上的妈妈们讲,这些是书房、厅上的东西,既归我打扫,便该我洗!”
声音细细弱弱,如同冬日书上最后一片残叶,飘忽著,眼看就要被寒风吹散了:“不打紧的————我在旧主家————也常.的————惯了————”说著竟还想把那双红肿如萝卜、指节处已绽开血丝裂口的手往冰水里探!
“放屁!什么惯了,什么该你洗!”金莲儿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口银牙几乎咬碎:“你是老爷心儿上的尖尖人,那浆洗房的黑心老货!打量你是新来的,又老实,专会拿软柿子捏!什么书房厅上的东西该你洗?放她娘的狗臭屁!她们是瞧著天寒地冻,想躲懒,把这要命的活计推给你这傻丫头顶缸!”她越说越气,嗓门也拔高了,在这静夜里格外尖利。
她死死攥著香菱的手腕子,硬是把那双冻得猫咬似的小爪子从冰水里拖出来,不由分说地塞进自己暖烘烘的怀里捂著,嘴里依旧不饶人地骂:“你也是锯了嘴的葫芦!她们叫你洗你就洗?这冰窟窿似的水,她们自己怎么不来试试?冻不死这群黑心烂肺的老虔婆!你瞧瞧你这手!还冻木了不疼”?再泡下去,这双手就废了!到时候看哪个主子还要你这残废丫头!”
金莲儿只觉一股恶气堵在嗓子眼,上不去下不来,噎得人发昏。
她猛地一弯腰,也不管那井水刺骨冰寒,两只手狠狠插进那堆湿漉漉、滑腻腻的织物里,死命往外一扯——“哗啦!”一声巨响,水四溅,淋淋漓漓洒了一地。
“走!”金莲儿一把攥住香菱那细伶伶的手腕子。
“跟我走!我倒要亲口问问那几个老歪刺骨、老白嚼,她们那几双贼爪子是叫狗叼了,还是灌了铅水?这般蹬鼻子上脸地作践人,真当我是泥塑木雕、死的不成?”
香菱被拽得一个趔趄,冻僵的脚在湿冷的石板上几乎站不稳根,口中慌乱地哀告:“姐————姐姐,使不得!算————算了吧,真————.————.为我————”那细弱的声音带著哭腔,活像被踩了尾巴的猫崽儿。
“算?怎么能算!”金莲儿猛地扭回头,一双眼睛在月光下灼灼放光,燃著两簇烧天怒火,恨不能將这寒夜的井台都点著了:“你不知,举凡大宅子里丫鬟婆子都是势利眼,你今日忍了这口腌臢气,明日她们就敢骑到你脖颈子上!”
“你忍得下,我可忍不了!她们欺你,便是欺我!”
她手上力道更添三分,拖著那轻飘飘、瑟瑟发抖的小身子,头也不回地撞进沉沉的夜色里,直直奔浆洗房那群婆子的住处而去。
金莲儿拽著香菱,脚下生风,恨不能一步就踏进浆洗房那低矮的耳屋里。
那浆洗房紧挨著后巷,平日里水汽蒸腾,混杂著皂角、汗馒和阴沟的醃攒气味,此刻夜深,只余下湿漉漉的阴冷扑面。
窗户纸透出昏黄摇曳的一点油灯光,里面影影绰绰,几个婆子正围著一只炭火將熄未熄的破泥炉子,嘴里嚼著舌根,手里纳著鞋底,好不自在。
金莲儿也不敲门,抬脚“哐当”一声,將那扇薄木板门踹得几乎散了架!
门板撞在墙上,震得房樑上的灰簌簌往下落。屋里几个老货唬得一跳,齐齐扭过头来。
“一群老东西!”金莲儿拖著香菱,直衝进屋子中央,一双喷火的杏眼在昏灯下扫过那几个惊魂未定的老脸—为首的陈婆子,惯会偷奸耍滑;李婆子,一张嘴比砒霜还毒;还有那张婆子,最是欺软怕硬。
“都给我滚起来!我倒要问问,你们那几双贼爪子是叫野狗嚼了,还是灌了铅水沉了井?竟敢把主子的体面物件,推给老爷书房里的伴读丫头洗!”
那陈婆子先是一愣,看清是金莲儿和香菱,慢腾腾放下手里的鞋底:“哟,我当是谁原来是金莲姑娘。这深更半夜的,火气怎地这般大?嚇煞老身了。”
她眼皮一翻,陪笑道:“姑娘这话说的没头没脑,什么主子的物件?我们浆洗房只管各房主子奶奶们的贴身衣物並粗使下人的衣裳,那书房、厅上的坐褥、
窗幔,本就是归打扫的人顺手料理,这是府里多少年的老规矩了————”
“放你娘的狗臭屁!”金莲儿不等她说完,一口啐在地上,唾沫星子险些溅到陈婆子脸上,“老规矩?就算是老规矩,可香菱儿是什么任人?她是老爷的房里人,你们分明是欺香菱新来,性子软和!那冰碴子水,你们这老皮老肉的不肯沾,倒推给一个细皮嫩肉的小姑娘去受冻?你们的心肝,怕是叫狗掏吃了!”
李婆子性子最急,被金莲儿指著鼻子骂,脸上掛不住,也跳了起来:“金莲姑娘!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她既是管书房的,那里头的物件脏了,她不洗谁洗?你去问问大娘,这么些年是不是这样?”
金莲儿怒极反笑,猛地弯腰,一把抄起墙角一个盛满脏水的木盆那水黑默、油腻腻,漂著皂沫和不知名的污物—“规矩?我今儿就教教你什么叫规矩!”
话音未落,她双臂发力,竟將那满满一盆腥臊恶臭的脏水,兜头盖脸朝著李婆子、陈婆子几个泼了过去!
“哗啦——噗嗤——!”
事出突然,那几个婆子躲闪不及,被泼了个正著!冰凉腥臭的脏水顺著她们白的头髮、油腻的脖颈直往下淌,灌进衣领子里,糊了满脸满身。
李婆子“嗷”一嗓子怪叫出来,陈婆子呛得直咳嗽,张婆子更是嚇得一屁股坐倒在水洼里,狼狈不堪。
“哎哟!我的老天爷啊!杀人了!杀人了!”李婆子抹著脸上的脏水,杀猪般嚎叫起来。
“金莲姑娘!你敢!”陈婆子也气急败坏,伸手就要来抓金莲儿的头髮。
金莲儿岂是吃素的?
她早就憋著一肚子火,见陈婆子扑来,身子灵巧地一侧,让过那枯爪,反手就揪住了陈婆子脑后稀疏的髮髻,死命往下一拽!
另一只手“啪”的一声脆响,一个结结实实的耳光就扇在了陈婆子那张布满褶子的老脸上!
“老虔婆!给你脸了!我今日就替香菱,也替这府里被你们作践过的丫头们,出出这口醃攒气!”金莲儿一边骂,又甩了两巴掌。
浆洗房里顿时乱作一团!
李婆子嚎叫著要来帮手,金莲儿一脚踹开旁边碍事的矮凳,抄起洗衣用的棒槌,劈头盖脸就砸过去。
只听得乒桌球乓,叫骂声、哭嚎声、器物碎裂声响成一片,在这死寂的深夜里格外刺耳。
“反了!反了天了!快来人啊!金莲这泼妇要杀人了!”陈婆子披头散髮,脸上带血,鬼哭狼嚎地往门外爬。
“吵吵什么!深更半夜,闹得闔府不寧,成何体统!”一个清冷威严的声音突然在门口响起。
眾人动作一滯,如同被施了定身法。
只见门口灯笼映照下,月娘披著一件银鼠皮袄子,旁边站著桂姐儿和小玉,正冷冷地扫视著屋內的一片狼藉:
水漫金山,盆倒桶翻,几个婆子如同落汤鸡般浑身脏污,陈婆子脸上还掛著血道子,金莲儿兀自拿著棒槌,胸口起伏,怒目圆睁,香菱则像只受惊的兔子左右拦著。
月娘的目光在金莲儿和那几个婆子身上转了一圈,最后落在香菱那双冻得红肿、此刻沾了泥污的手上,眉头不易察觉地蹙了一下。
她没问缘由,只对著金莲儿淡淡地说:“金莲,把手里的东西放下。”
金莲儿见是月娘,赶紧將棒槌往地上一扔,发出“哐啷”一声响。
“夫人!您可要为我们做主啊!”陈婆子如同见了救星,连滚带爬扑到月娘脚下,指著金莲儿哭诉,“这金莲,无缘无故打上门来,泼了我们一身脏水,还动手打人!您看看我这脸————还有李妈妈她们————这泼妇是要我们的老命啊!”
李婆子、张婆子也赶紧跟著哭嚎附和,把脏水全往金莲儿身上泼。
月娘没理她们,转而看向金莲儿:“金莲,你说。”
金莲儿深吸一口气,指著那几个婆子,声音依旧带著火气:“大娘明鑑!这几个老虔婆,倚老卖老,狗胆包天!月娘您明明只吩咐香菱打扫书房灰尘,她们倒好,把书房里所有的坐褥、垫巾、窗幔,一股脑全推给香菱洗!”
“深更半夜,冰天雪地,逼著香菱在井台边用冰水搓洗,那手都冻得不成人形了!奴婢实在气不过,才来与她们理论!她们非但不认错,嘴里还不乾不净,奴婢一时气急,这才动了手!夫人若不信,香菱的手就在那儿,那堆没洗完的物件还在井台边!
香菱怯生生地抬起红肿的那双手,在灯笼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李桂姐轻声说道:“香菱儿不只洗这一日了,我刚进府里来,也见过一次,还以为是府里的规矩....没有多说”
月娘的目光扫过那双手,又冷冷地看向那几个婆子。陈婆子等人被月娘看得心里发毛,还想狡辩:“夫人————这、这规矩————”
“规矩?”月娘的声音不高,却带著一股寒意,打断了陈婆子的话,“是府里的规矩没错,但也看是对什么人,是让你们这般顺手”支使老爷书房伴读的?你们浆洗房的手,是比主子房里的人还金贵了?”
“就算老爷还未给名分,但那冰水,你们洗不得,倒让一个识文断字、近身伺候老爷笔墨的丫头去洗?好大的胆子!”
最后四个字,月娘说得又轻又慢,却像冰锥子一样扎进几个婆子心里。
陈婆子等人顿时哑口,面如土色,知道这“规矩”二字,在月娘这里搪塞不过去了。
月娘不再看她们,对金莲儿道:“你性子是急了点,动手更是不该。念在你一片护人之心,又是初犯,罚你半月月钱,长长记性。”
她又转向那几个抖如筛糠的婆子,声音更冷:“你们几个,倚老卖老,差事推諉,还巧言令色,败坏府里规矩。每人扣半年月钱!从明日起,书房、大厅所有需浆洗的物件,全归你们浆洗房按时按质做好!若再敢推諉懈怠,或私下作践他人,別看你们年龄老,一棍棒下去打死也是活该,滚下去!”
“是——是——谢夫人开恩————”几个婆子如蒙大赦,又心疼那半年的月钱,哭丧著脸,互相搀扶著,狼狈地退了出去,连地上的脏污也顾不得收拾。
月娘这才看向身旁的香菱,语气缓和,拍了拍她的小说:“香菱,你起来。
手冻坏了,回去用热水好生泡泡,抹点冻疮膏子。这几日不必来听吩咐了忙过年的事了,书房歇息几日看看书,写写字。”
“谢————谢大娘————”香菱声音细如蚊蚋,带著哽咽福了福。
月娘点点头说道:“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说著转身离开。
心中也在思虑,看来等官人回来要商量著,开始要给府里的丫鬟分一分身份了,不然以后宅子越来越大,人越来越多,这样的事情还会更多。
灯笼的光晕隨著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黑暗的廊下。
金莲几胸中那口恶气算是出了大半,看著那几个老货受罚,心里也解气。
她走过去,拉著还在发抖的香菱,拍了拍她身上的灰:“走,回去!”
香菱冰凉的小手被金莲儿温热的手攥著,一股暖意从手上蔓延到心里。
月光依旧惨白地照著,將两人一高一矮、相互扶持的影子,长长地拖在冰冷的青石板上。
回到自己房里,金莲儿翻出一个小瓷瓶,里面是上回老爷赏的玫瑰香膏子,她平日里都捨不得用。
挖了一大坨,不由分说拉过香菱的手,就往那红肿的地方抹:“抹上!这好东西,治冻疮最好!明儿再找点艾草灰给你敷上!”
香菱看著那晶莹的膏体,闻著那馥郁的香气,再看看金莲儿虽骂骂咧咧却动作轻柔的样子,眼泪又涌了上来,却不再是委屈,而是暖融融的一片。
而大官人此时渡步到客厅,深深的嘆了口气!
这叫个什么事!
一巴掌下去。
赵福金痛得浑身猛地一弓!
带著高烧的灼热气息和一丝猝不及防的颤抖,她死死攥紧了身下的锦褥又昏了过去,嚇了大官人一跳,好在嘆了嘆鼻息,听了听心跳,这才放心下来。
雪白的皮肉上立时浮起一个鲜红的印子,边缘还泛著指痕!
恍若一块上好的羊脂玉被硃砂印狠狠摁了个透那红痕深深陷进白肉里,周遭肌肤受惊般泛起一片细密的鸡栗疙瘩,衬著那白底红痕竟有种残酷又香艷的靡丽。
大官人整了整被赵福金揉皱的衣襟,大步跨出房门。
“玉娘!”他扬声一唤,那伶俐的妇人一直內厅等候,闻声忙不叠地碎步上前,垂手听命。
“里头那位,”大官人下巴朝屋內一点,声音压得又低又沉,“你仔细看顾著!烧若退了,餵些温软汤水。若还烧得糊涂——”
他顿了顿:“用冷帕子勤擦著身子降温。记著,她身份非同小可,掉根头髮丝儿,你都得拿命赔!!”
玉娘立时明白了轻重,忙堆起十二分的小心,屈膝道:“大人放心,民妇今夜就抱著铺盖捲儿,睡在这外间地上支应著,保管耳不落音儿!”
大官人鼻子里“嗯”了一声,让她下去。
隨即又喊来扈三娘!
俩人直奔后院那间不起眼的东厢房。
进了屋,目光在灰尘和阴影里扫视,对扈三娘低声说道:“找一找地窖和在哪儿。”他手指重重点过角落、床底、墙壁,“比如格外乾净的地界儿,或是沾著外头新鲜湿泥的痕跡!”
扈三娘应声而动,身手利落如狸猫。
她伏低身子,指尖在冰冷的砖地上细细摸索,不过一盏茶的功夫,只听她在床榻阴影下低呼一声:“爷!这里有活板!”
大官人上前,果见一块与周遭严丝合缝的厚实木板,扈三娘抠住暗藏的铁环一声发力!
沉重的地窖门应声而开,露出黑洞洞向下延伸的石阶,一股混杂著铁锈、尘土和阴冷的霉味儿扑面而来!
但见数十口黑沉沉、硕大无比的酸枝木箱子,整整齐齐码满了大半个密室!
箱盖並未锁死。
大官人屏住呼吸,用刀尖猛地撬开最近一口一火光照耀下,箱內赫然是层层叠叠、黑泛著幽冷金属光泽的厚重甲片!
那形制粗獷狰狞,覆盖范围极大,不仅有人穿的全身重鎧,连马匹的面帘、
鸡颈、当胸、马身甲乃至搭后都一应俱全!
甲片上特有的契丹纹饰和磨损痕跡刺眼无比!这分明是辽国最为精锐的“皮室军”专用的连人带马重骑兵!
“嘶————”大官人牙缝里迸出一丝寒气,脸色瞬间变得铁青!
看来那位耶律大石带来的还不止是轻骑,还是一只皮室军”。
史文恭倒是介绍过,这种继承了中亚和西域的冷锻技术。通过反覆锤打熟铁,使其表面硬化,形成异常坚硬的甲片,而非中原常用的热锻淬火。
可通常这种皮室军”需要大量的后勤队伍才能运作,不是单单一只骑兵可以的。这耶律大石的谋划,绝不只是聚拢北地绿林豪杰这么简单。难道还有辽人在这北地??
他“啪”地一声重重合上箱盖,那巨响在密闭空间里迴荡,震得人心头髮颤。
他转身走出地窖喊来府上家庭护卫头子徐莽!
大官人指著地窖口,声音压得极低:“听著!立刻!把庄子上所有能用的马车、骡车,全给爷聚齐!带上所有兄弟不用跟著我了!”
“休息三个时辰后出发,把这两个密室里的箱子,一个不落,给老子押回府里交给来保和大娘!告诉他们不要打开存在院子便是!”
“这是天塌下来的干係!路上给老子眼睛放亮,嘴巴闭紧!谁敢多看一眼,多问一句,或是走漏了半点风声”
他看了一眼徐莽,徐莽心中一凛!
“是!爷!小的拿脑袋担保!”徐莽轰然应诺,额头青筋都暴了起来,转身就要去张罗。
大官人见他走后,对扈三娘说道:“三娘,这东西关乎我身家性命,单让他们这群人押运,我心中不放心。我需要你!你不用隨我去济州了,护著他们回到清河,出发后一路不停,送完再赶来匯合。倘若路上有人有什么別样心思,或者擅自查看箱子,你即刻一刀杀了,不用顾虑!”
扈三娘一听,心头猛地一撞,恰似那檐下铜铃被疾风扫过,嗡然作响。
她一双俏目定定地望著大官人,只觉一股滚烫的热流自脚底直衝顶门心,那耳根子先就“腾”地一下热辣辣烧將起来,比那新染的红绸还要艷上三分。
暗道:“天爷!他————他竟连贴身的家中护卫都信不过?反將这泼天也似的干係,全副身家性命,都只託付於我扈三娘一人之手?”
一股难以言喻的酥麻与欢喜,如同春蚕吐丝,细细密密地缠绕了她的心肝。
又像初绽的桃瓣儿,怯生生、甜丝丝地在心湖里漾开,臊得她忙不叠垂下眼帘,长睫如蝶翅般微微颤动,遮住了满眼的星光水色。
她想:“他待我终究不同!这般天大的机密,身家性命所系,竟只肯託付於我————显是把我当作了最最贴心知意的人儿。”
一念及此,那被信任的熨帖与荣宠,便如暖酒入喉,四肢百骸都舒坦起来,著看大官人的眼神,也似那春水初融,波光瀲灩,平添了十二分的柔媚与依恋。
只觉得能为他分忧,为他担这天大的干係,便是立时死了,也是甘愿的。
她强按下那擂鼓似的心跳,稳住微微发颤的嗓音,深深万福下去,再抬头时,自光已如淬火的精铁,透著一股子决绝与凛然!
点头沉声道:“老爷放心!此物在,三娘在!便是粉身碎骨,也定將它安安稳稳送回清河!路上但有半点儿风吹草动起了歹心,定教那些杀才知道三娘这口刀有多利!”
这句话如此郑重,便连她自己和大官人都没发现,喊上了老爷!
大官人笑道:“倒也不必如此,倘若真遇到事情,你的命命是最要紧的事,哪怕掉了一根头髮丝都不允许!!”
这话如同滚油滴入冷水,在扈三娘心湖里“滋啦”一声炸开!
她只觉得脸上那刚褪下去的热气“腾”地又翻涌上来,比方才更甚,连脖颈都染上了霞色。一颗心在腔子里擂鼓般乱撞,脑子一片空白?臊得她手脚都没处放。
她慌忙低下头,结结巴巴道:“我——我我——大人,外头——外头好像有事,我——我出去会!”
声音细若蚊蚋,话未说完,人已像受惊的兔子般扭身就往外跑。
大官人瞧著她慌乱的背影,嘴角噙著一丝笑意,扬声道:“跑慢些!顺道把你哥叫来內厅!”“知——知道了!”扈三娘的声音远远飘来,人已消失在廊角。
大官人看著密室入口,重新將那精巧机关遮掩好,这才整了整衣袍,踱步出来。
唤过一个官兵:“去,把关胜给我请来。”
不多时,关胜大步流星而来,身姿挺拔如松,抱拳躬身,行了个標准的武人礼:“大人!关胜在此,听候吩咐!”
大官人微微頷首,目光在他身上扫了一圈,仿佛在掂量一件趁手的兵器,语气隨意地问道:“嗯,来了。吃饱喝足了吗?”
关胜一愣,没想到大人开口问这个,隨即老实答道:“回大人,酒足饭饱,浑身是劲儿!”
“好!”大官人踱了两步,忽地站定,单刀直入:“关胜,你这一身好本事,拳脚刀马都来得,为何到了今日,还只是个小小的九品巡检?”
这话像根针,精准地扎进了关胜最尷尬的痛处。
他脸上那点爽朗的笑容顿时僵住,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声音不自觉地低了几分,带著几分憋屈和无奈:“这————回大人话,卑职————卑职也实在不知!对上峰,该有的礼数从未短少,逢年过节,该孝敬的————也从未落下,可————可这些年,就像那磨坊里的老驴,原地打转,寸步难进!卑职————卑职也著实苦闷!”
大官人笑道:“我也不瞒你,我府里管家的官身,是个七品校尉!我身边几个得用的家养小廝,跟你一样,也都是九品巡检的衔儿!”
这话如同一个响亮的耳光,扇得关胜麵皮紫涨,脑袋“嗡”的一声。
七品管家?九品家奴?
自己苦熬多年,拼死拼活,竟和人家府里伺候人的奴才一个品级?
一股难以言喻的酸楚瞬间衝上头顶,只觉得这官袍穿在身上,比那囚衣还要沉重丟人!
他嘴唇哆嗦著,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大官人將他的窘態尽收眼底,知道火候到了,换上一副招揽贤才的郑重神色,语气斩钉截铁:“关胜!我也不跟你囉嗦绕弯子!我看你是个人才,埋没可惜了。我想把你调出来,跟著我干!替我办事!你可愿意?”
他顿了顿,不容置疑地补上关键一句:“你若点头应下,我明日就下调令!”
关胜心中猛地一跳!那巨大的羞耻感还未散去,但一股狂喜却像地底的岩浆,瞬间衝破压抑,喷涌而出!
他方才那点憋屈、茫然、无措,在这“调令”二字面前,顷刻间烟消云散!
这还用考虑?
关胜不是蠢人。
在这官场市井摸爬滚打多年,早练就了一副火眼金睛。
眼前这位大人,气度非凡,言谈举止透著深不可测的威势。
他既然能轻飘飘说出“七品管家”、“九品家奴”,又能许诺“明日下调令”,这背后的能量,绝非他一个苦哈哈的九品巡检能想像的!
倘若他没这通天的本事,根本不可能调动得了自己!
但凡他能调动,就绝对是天大的本事!跟著这样的人物,还愁没有出头之日?
关胜再无半分犹豫,猛地一撩战袍前襟,“噗通”一声单膝跪地,抱拳过顶:“大人!关胜愿为大人效死力!从今往后,唯大人马首是瞻!刀山火海,绝无二话!”
大官人看著他跪伏在地的魁梧身躯,满意地点点头,上前一步,亲手將他扶起,拍了拍他那厚实的肩膀,笑道:“好!跟著我,亏待不了你!起来吧!”
“你且去前厅,替我紧紧盯著那起子傢伙!待我料理完手头事,便连夜提人审问!”
关胜抱拳沉声应道:“是!”隨即转身,大步流星地去了。
第247章 泼天收穫,西门府眾女起风波
同类推荐:
白昼焰火(熟男女性爱日常,女出轨,高H)、
断奶(骨科 1v1)、
征服男校可行性分析(GB)、
被我养育的小萝莉们(未删节1-117章+番外篇)、
死了一个娱乐圈男演员之后、
远山温柔、
那一日大雪、
冷翡翠与北冰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