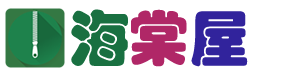內阁首辅黄立极府邸,书房。
烛火通明。
黄立极放下手中的茶盏,听著长子黄蘅若稟报信王府的最新动向。
“持斋祈福?”
黄立极捻著鬍鬚,微微頷首。
是个知礼感恩,又有脑子的。
与他那日在乾清宫见到的形象逐渐重合。
在兄长病榻前真情流露,又在关键时刻措辞严谨。
比外界传言中那个多疑刻薄的少年亲王,要强上太多。
“你说信王殿下收了礼,但是没有回应?”黄立极看向次子黄藻,確认道。
黄藻回答:“是,父亲。各家送的,无论轻重,王府皆收下,却无只字片语回復。听说王府库房快摆不下了。”
黄立极沉默片刻,心中念头飞转。
“收礼不拒,概不回应”的姿態,是一个极其精明的信號。
既安抚了那些急於投靠,心怀忐忑的官员,避免了新君继位前可能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动盪。
未给任何人任何明確的承诺,將全部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
这份沉静与老练,出乎他的意料。
天启也是当了几年皇帝,才慢慢有了这种境界。
“父亲?”长子黄蘅若见他久不说话,出声唤道。
黄立极抬眼看向两个儿子,目光沉静:“魏忠贤那里,暂时不要往来了。”
他缓缓开口,“府中与魏忠贤过往甚密的文书、信函,该烧的,都烧了吧。”
隨后,他吩咐次子黄藻:“去,严令我们的门生故旧,在新皇正式登基之前,都安分守己,说两句好话,不要轻举妄动,一切观望为上。”
(请记住 读小说就上 101 看书网,101??????.?????超顺畅 网站,观看最快的章节更新)
......
次辅施凤来府上,则是另一番光景。
施凤来问垂手侍立的儿子:“送往信王府和魏公公府上的那两份礼物,都確保送妥帖了?”
“回父亲,均已办妥。信王府那份是公开呈送,魏公公那份是秘密送达,新君那边更为贵重。”
施凤来嗯了一声,心中稍定。
他准备这两份厚礼,意在两边下注,无论风嚮往哪边吹,他都能有所依仗。
在这局势未明之际,脚踏两只船虽风险不小,却也好过在一棵树上吊死。
“让幕僚和门下们都警醒著点,”他吩咐道,“密切关注黄阁老那边的动向,还有魏公公的反应。待风向清晰些,我们再做最终决断。”
群辅张瑞图的府邸。
作为以书法諂媚魏忠贤而得以上位的人,张瑞图这些日子可谓寢食难安。
他第一时间就不惜血本,备下了一份重礼,一方前朝古砚,早早送入了信王府。
同时,他动用了所有同乡、同年等关係,拐弯抹角向信王府传递效忠之意,也在士林鼓吹“吾弟为尧舜”的口諭。
相比之下。
另一位群辅李国普则最为轻鬆。
他虽与魏忠贤是同乡,但在阉党势大时亦每持正论,並未同流合污。
此刻倒也心中坦然,静观其变。
......
英国公府。
张之极刚刚送走了一拨前来探听消息的勛贵子弟。
花厅內,头生华髮的英国公张维贤端著参茶,慢悠悠问:“都走了吗?”
张之极擦了擦额角的细汗,回道:“都走了,父亲。大家心里还是有些顾虑,信王殿下那边,至今没有任何回话。”
张维贤笑了笑,並不意外:“礼呢?都收了吗?”
张之极道:“都收了!不只是我们勛贵各家,內阁的、六部的、甚至,甚至连魏忠贤那边派人送的,只要是送去的,信王府一概都收下了。”
“收了就好。收了就好啊。”
张维贤连说两句,脸上笑意更深。
他不怕朱由检聪明,就怕他不够聪明,將人都得罪光。
“传我的话给京营里我们的人。”
张维贤神色一正,对儿子说道,“京营兵马,我们的人,必须牢牢握在我们手里,绝不能听从魏忠贤或其党羽的调遣。”
这不只是他个人的態度,更是整个勛贵集团的意志。
作为与国同休的勛戚之首,维护皇权平稳过渡,护卫京城安全,是他们不容推卸的责任,也是他们核心利益所在。
张之极点头应下,又道:“父亲,京营中那些由太监提督的营头,以及一些依附魏忠贤的武將,如今也有些乱了阵脚,不少人也偷偷往信王府上送了礼。”
“都收了?”张维贤问。
“都收了。”
“收了就好,收了就好。”
张维贤再次重复道,心中愈发安定。
朱由检表现得越沉稳,越有手段,他越满意。
如今局势,不做迂腐君子,实乃国家之福。
......
紫禁城,西华內门附近,咸安宫。
此处为奉圣夫人客氏居所。
殿內陈设奢华,薰香浓腻,却驱不散那股惶惶不安之气。
客氏虽年近四十,但因保养得宜,看上去不过三十来岁,风韵犹存。
此刻却是花容失色,全没了平日“老祖太太千岁”的威风。
她拿著丝帕,不住按著眼角。
“你说,皇上怎么,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魏忠贤坐在一旁,眉头紧锁。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皇上落水后本来身体好的差不多,怎会被王恭厂那场莫名其妙的巨爆一惊,就连同皇嗣一起.......
更让魏忠贤不安的是,王府內消息有点难以打探。
重金贿赂徐应元,也是一波三折。
好在礼物朱由检这位新皇都接受了,让他稍微心中安定。
魏忠贤勉强收拾起纷乱的心绪,对客氏道:“现在说这些还有何用?信王那边既然收了咱家的礼,就说明新君不是那等油盐不进,不能伺候的。”
“你没听当时万岁爷传位时,他说了『遵旨』吗?这话,他是听进去了。”
他在安慰客氏,也是安慰自己。
眼下,他的东厂番子回报,他麾下的“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辈,无不人心惶惶,已有不少人开始暗中另寻门路。
客氏不安扭著帕子,像是发狠又像是绝望:“他可是只谢了张皇后那个小娘皮!闭门持斋,也只和坤寧宫有沟通!我们就这么干看著?他收了礼是不假,可没有回话啊!只收不理,这算什么態度?”
魏忠贤心中烦躁,耐著性子道:“我已让王体乾、李永贞他们紧紧盯著呢。我也让人仔细分析了那份送礼人员的名单。”
他没说的是,司礼监掌印王体乾表面上依旧恭顺,但如今总觉得隔了一层。
而李永贞,因为当初奉命修建信王府时贪墨了些银钱材料,是最早嚇得魂不附体,赶紧补送重礼的。
对他们这些权阉来说,当初欺负一个无权无势的藩王根本不叫事。
只是没料到,这藩王转眼就要成为手握他们生杀大权的皇帝了。
该死的落水啊!
魏忠贤难受,多少皇帝都坏在了这落水上!
......
兵部尚书崔呈秀府邸。
无论是府內僕役,还是朝堂同僚,所有人都处在一种如履薄冰的压抑气氛中。
崔呈秀作为魏忠贤麾下地位最高的外朝官,没有任何退路。
长子崔鐸实在受不了这种煎熬,闯进书房急声道:“父亲!我们难道就什么都不做,坐以待毙吗?”
崔呈秀面色阴沉,呵斥道:“慌什么!”
他压低了声音,“我早已秘密派人接触信王府,送上了厚礼,並暗示我执掌兵部,熟悉京营及边务,愿为新帝效犬马之劳,肝脑涂地!”
他顿了顿,又道:“我还派人去了信王岳丈周奎周指挥府上,不仅送了钱,还帮他家干了点杂活,刨了地。新皇登基,总要用人办事的。”
堂堂兵部尚书,去给人刨地。
一个兵部尚书的投效和全部忠诚,难道新皇真的毫不动心吗?
......
锦衣卫都指挥使田尔耕,和指挥僉事许显纯这两位酷吏头子,更是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不仅给信王府送了远超常例的厚礼,更是几乎踏破了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崇禎岳父周奎家的门槛。
各种討好巴结,只求能留得一线生机。
他们比谁都清楚,一旦魏忠贤倒台,自己手上沾满东林党人鲜血的下场会是什么。
同时,他们已开始秘密下令,销毁一些敏感的卷宗和刑狱记录,抹去那些过於血腥的痕跡。
......
八月十八日。
也不知是从信王府的哪个环节泄露出的风声,一则消息悄然在京城各大府邸间流传。
信王府收礼,不仅有专人记录礼单物品,还详细记录了每一日、每个时辰的送礼批次与人员。
特別强调了批次。
轰!
整个京城的气氛,顿时变得更加波譎云诡,暗流汹涌。
.......
司礼监值房內。
鎏金兽首香炉青烟裊裊
魏忠贤坐在紫檀木扶手椅上,手指无意识敲击著光滑的桌面,听著亲信带来的消息,脸色阴晴不定。
“记录名单也就罢了,为什么还要分批次、记时辰?”
魏忠贤喃喃道,变得有些魂不守舍。
他不由得一愣,这种感觉,他有点熟悉,他用尽全力去揣摩天启帝的心思和喜好才会有。
李永贞站在下首,闻言急忙问道:“这消息,是真的吗?”
他心中也是七上八下。
如今的信王府,不知用了什么法子,竟像是铁桶一般,再不像过去那样消息灵通,任由宫內朝堂窥探。
往昔安插的眼线,近来都难以传递出有价值的讯息。
魏忠贤瞥了他一眼,语气带著一丝疲惫:“这是徐应元那老货,好不容易才夹带出来的消息。”
为了这个消息,他足足花了一万两雪花银。
如今信王府的心腹內侍外出,必定是两人同行,相互监视,等閒难以单独接触。
徐应元也是眼红那如流水般收进来的礼物,自己却捞不到多少油水,才甘冒风险,一点点將消息释放出来。
光是把这个信息传出来,就花了好几天工夫。
想到这里,魏忠贤心头更加不安。
徐应元身为信王府承奉正,內侍之首,传递个消息都如此艰难,这本身就说明信王驭下极严,手段厉害。
徐应元,恐怕已经彻底倒向新主子了。
王体乾站在一旁,低眉顺眼,但想到李永贞最早送上巨额赔罪银,就忍不住话里带著刺道:“李公公倒是跑得快,手脚麻利。”
李永贞脸上挤出一丝难看的笑容:“王公公说笑了。奴婢当初督修王府,確有疏忽之处,如今只求王爷能给个侍奉的机会,便是倾家荡產也心甘情愿。”
“我们做奴婢的,不就盼著主子能给条活路,给个机会嘛?”
他这话看似对王体乾说,眼睛却偷偷瞟向魏忠贤。
魏忠贤冷眼旁观著这一切,心中一片冰凉。
朱由检还没继位,只是做出姿態,如今的局面,除了自家那个不成器的子侄,他还能完全相信谁?
他不知道手下这些“十狗”、“四十孙”里,有多少人已经背著他,悄悄向信王府递了投名状。
就连原本对他唯命是从的阁臣,如今除了必要的公事,也已经开始有意无意避著他走了。
世態炎凉啊!
......
內阁首辅黄立极的府邸书房內,烛火摇曳。
黄立极眉头紧锁。
这位尚未正式登基的新君,心思之深沉,手段之老辣,远超他的想像。
“收礼”尚且能理解,这“分批次记录”之举,是无意流露的严谨,还是刻意为之的震慑?
有点摸不透。
长子黄蘅若在一旁低声询问道:“父亲,这份礼单,最终会变成秋后算帐的名单,还是將来敘功拔擢的名录?我们要不要,再加重分量,送一份厚礼?”
黄立极缓缓摇头,將那份名单放下。
“稍安勿躁。”
无论如何,他此刻还是大明的首辅,文臣之首。
相比那些毫无根基的厂臣,他总归还有几分退路和体面。
......
南城兵马司副指挥周奎的宅子里,却是另一番光景。
周奎看著库房里堆积如山的箱笼,里面是白花花的银锭和一叠叠的银票,激动得双手发抖,嘴唇哆嗦。
“八万两,八万两啊!”
他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
那些平日里眼高於顶的官员,什么“五虎”、“五彪”,如今都和他称兄道弟,各种请託应接不暇。
儿子周鉴却有些抱怨:“父亲,姐姐如今在王府里,连个面都不让我们见。收了这么多钱,答应了不少事,可姐姐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怎么帮他们办事?”
继妻朴氏到底关心亲女儿,谨慎些,忧心忡忡道:“老爷,咱们收这些,会不会出问题?要不要挑些好的,给王爷府上送去一些?”
闻言,周奎不耐烦摆手:“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咱们女儿马上就要当皇后了!我就是国丈!这些都是他们应该孝敬我的!”
他顿了顿,又得意地补充道:“而且你忘了?最早得到宫里確切消息的时候,我可是第一时间就备了重礼上门的!”
当然,他没好意思说,那时的“重礼”,和如今日进斗金的规模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值一提了。
.......
而原本因为新君“收礼”而蠢蠢欲动的清流言官们,得知“分批次记录”的消息后,不少人都愣在了当场。
他们原本以为,新君收礼,且只回復皇后之举,是对百官敞开大门的明確信號,是拨乱反正的开始。
“眾正盈朝”的时刻即將到来。
他们甚至已经准备弹劾阉党的奏章,只等新帝登基便开始试探。
可这“分批次记录”,这意味著新君不仅仅是在收礼,更是在审视、在甄別!
他们这些清流,有钱也不能送礼啊!
只能继续沿用老办法,以“星变”、“灾异”为名,在奏疏中隱晦攻击阉党。
......
一些与江南联繫紧密的漕运和商贾势力,则开始以更快的速度向南方传递消息。
隨著天启帝落水,他们早已建立起一条高效的信息渠道。
更隨著重病,这条渠道的信息更新频率已经从半个月一次缩短到一天一次。
只是,再快的速度,消息传到江南也需要时间。
此刻,仅仅是从信王府释放出的这一点点信息,已经让他们感觉到,这位即將登基的新皇帝,心思深沉,难以揣摩。
如今的朝野,经过魏忠贤数年的“物理清理”,东林党人几乎已经从朝堂上消失了。
內阁三人被视为“阉党”,六部堂官也多是依附魏忠贤者。
东林党的骨干力量全数窝在江南,或隱居,或罢官。
如果这些人不回来,仅凭朝中剩下的几只“清流”小猫,想要抗衡盘根错节的阉党势力,难如登天。
......
那些原本依附於阉党的其他文官势力,则抓住了这个机会,更加积极送礼。
他们在名帖中开始撇清与魏忠贤的关係,声称心向圣学,表达忠心。
“分批次收礼”的消息悄然传开,释放的政治信號,在天启帝身体越来越差之际,被急剧放大。
早送礼的人惊喜若狂,不早不晚的悵然若失,观望迟疑的开始后悔。
而且看到信王府的库房已经填满,大门依然为后续的送礼者敞开著,只是提高了门槛。
甚至有传言,新君爱吃现杀的黄牛肉。
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新君不是在拒绝,而是在筛选!
现在不送,意味著將来可能被划入“不可用”之列!
於是,除了少数极其爱惜羽毛,自作清高的官员,即便是那些以清廉著称的文臣,也或多或少备上了一份“礼节性”的礼物。
第二波送礼的浪潮如同海啸般涌向信王府,其涉及人数和礼物总额,远远超过了第一波。
.......
信王府,內书房。
八月二十一日的上午,阳光透过窗欞,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光影。
“王府放不下,再买几套宅子就是。”
朱由检隨意对周王妃道。
看著王承恩最新整理呈上的礼单匯总名录,他没有先看財物,而是重点名单,確定几个重要人物都送了,甚至有魏忠贤的心腹送上了两份。
大势已定!
朱由检微微点了点头。
然后才是財物,光是银票,折算下来就接近五十万两之巨!
这还不包括那些难以估价的古玩字画,珍奇宝物。
至少有百万財货!
送礼者遍布朝野,文官、勛贵、宦官,甚至连一些嗅觉灵敏的商贾都掺和了进来。
只是后者门槛很高,万两之下,不收!
朱由检心中宽慰,谁要敢说明末没有“忠君体国”之辈,他真想喷他们一脸!
人家只是缺少一个机会!
啪!啪!啪!
书房外间,传来清脆的掌嘴声。
徐应元跪在冰冷的地砖上,一边用力扇著自己耳光,一边带著哭腔道。
“殿下!殿下!奴婢猪油蒙了心!奴婢该死!奴婢该死啊!”
其他內官看著悽惨的徐应元,心里舒畅。
从龙之功啊,你徐公公没把握住!
既然“分批次记录”的消息能泄露出去,內部自然要清查。
徐应元这点伎俩,在朱由检眼中根本无所遁形。
如果徐应元不传出去,朱由检都要指示人去做了。
他都没有想到,画了一个饼,说了两句好话,再初步建立一套反馈机制,內府就安定了。
朱由检没有看他,只是淡淡开口道:“起来吧。”
然后对內官承诺道:“王府所收之礼,將来皆会冲入內库,用於国事。”
虽然內库是皇帝的私库,但皇帝的事就是国事。
朱由检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在任何场合,承认自己是在搜刮钱財。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要占据道德和法统的制高点。
徐应元如蒙大赦,却又不敢完全放心,连忙磕头道:“殿下明鑑!奴婢愿意献出魏忠贤给的所有贿赂!殿下,奴婢只是一时贪財,和魏忠贤绝无更深瓜葛啊!”
“是个懂事的。”
朱由检不置可否评价了一句,能听懂暗示就好。
他站起身,没有再理会跪在地上的徐应元,径直离开了书房。
徐应元看著朱由检离去的背影,直到看不见了,才瘫软下来,感觉后背已被冷汗浸湿。
等到心腹將他拉起来,他这才发现,自己把自己的脸都扇肿了。
他清晰感觉到,隨著宫里天启帝的身体越来越差,自家这位王爷身上的威势就越来越重,令人敬畏。
徐应元此刻肠子都悔青了,不该贪心,真不该贪那点银子啊!
狗日的魏忠贤,他日你老小子不要落在我手里!
他挣扎著爬起来,赶紧爬著向王妃周氏请罪,將没来得及捂热乎的银钱,一股脑儿全都上缴了过去。
.......
八月二十二日,午后。
紫禁城带著不祥的意味。
天启皇帝朱由校,已然弥留。
坤寧宫內,张皇后强忍著悲痛,立刻派遣心腹太监,火速出宫前往信王府报信,让朱由检准备入宫,並且嘱咐他自带麦饼。
同时,司礼监掌印王体乾和秉笔李永贞也不敢怠慢,一边安排宫禁事宜,一边催促內阁准备发布天启皇帝擬好的遗詔。
而魏忠贤却失了魂一般,呆呆坐在那里,望著天空的方向,眼神空洞,不知在想些什么。
信王府中。
朱由检接到了皇后派太监传来的话。
“知道了。”
然而,他並未丝毫准备动身的想法。
他心中已有定计。
王府堆不下的礼物,已经说明所谓阉党就是笑话。
皇后急,是因为说到底就是个妇人。
而且皇后也只是沾了天启帝皇权的光,她不是怕魏忠贤,而是厌恶和她同生態位的客氏。
朱由检不是文官,也不是后宫!
他才是皇帝!
是別人要怕他!
朱由检要效仿当年的世宗嘉靖皇帝,就在这信王府中,等待百官前来朝拜,完成权力的交接。
也给內阁文官、厂臣太监向他邀宠的机会。
第三章 朱百万
同类推荐:
我有一剑、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全息游戏的情欲任务(H)、
四大名著成人版合集、
都市偷心龙抓手、
斗罗大陆III龙王传说、
【电竞】信息素说我们天生一对、
宝宝,选我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