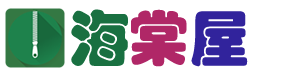潯阳城下,战云密布。
寧国军大营连绵数里,那黑色的“刘”字大旗在凛冽的江风中猎猎作响。
中军大帐內,死一般的寂静。
帐外的秋雨並未完全停歇,残水顺著毡布的纹理匯聚成股,滴落在泥地上,发出单调而沉闷的“啪嗒”声。
这声音在空旷的帅帐里被无限放大,像是一把钝刀,一下一下敲在人的心弦上。
数盏儿臂粗的牛油巨烛在铜灯台上燃烧,偶尔爆出一朵灯花,炸裂的轻响都会让帐內的空气隨之一颤。
“报——!”
亲卫掀帘而入,带进一股潮湿的水汽。
“潯阳城內有信使求见,自称是秦裴將军的亲侄,秦安。”
刘靖心头一跳,目光与身旁的袁袭一触即分,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火候,到了。
“传。”
片刻后,一名未著甲冑的青年大步入帐,正是秦安。
他进帐后不敢抬头,甚至不敢看周围那些杀气腾腾的武將,对著上首那道端坐的身影,纳头便拜。
额头重重磕在冰冷的毡毯上,发出一声闷响。
帐內依旧寂静无声。
秦安已经跪了足足一盏茶的功夫。
汗水顺著他的鬢角滑落,流进眼睛里,蛰得生疼,但他不敢擦,甚至不敢眨眼。
在他左侧,一股浓烈的血腥气混合著铁锈味扑面而来。
那是柴根儿。
这位传说中能手撕虎豹的悍將,正按著腰间的八棱骨朵,虎目圆睁,呼吸粗重。
秦安毫不怀疑,只要上首那位节帅一个眼色,自己的脑袋下一刻就会像个陶罐一样被砸得粉碎。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上首的刘靖没有说话,身旁的袁袭没有说话,连那煞气冲天的柴根儿也只是死死地盯著他。
这种沉默,比任何酷刑都更折磨人。
秦安的后背已经完全被冷汗浸透,他甚至能感觉到心臟在胸腔里狂跳,那声音大得他自己都听得见。
他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下去了。
再等下去,不等对方发话,自己这口气可能就先泄了。
他猛地一咬舌尖,剧痛让他混乱的思绪清醒了几分。
此刻开口,便是箭已离弦,再无回头之路。
他抬起头,迎著那道深不见底的目光,声音因极度的紧张而显得沙哑。
“回……回稟节帅!”
秦安艰难地吞咽了一口唾沫,强行稳住颤抖的气息,才继续说道:“家叔常言:『良禽择木而棲,贤臣择主而事。』”
“昔日家叔受杨氏厚恩,本欲结草衔环以报。”
“然,国祚不幸,徐温奸贼当道,弒主於內,囚君於上,更视我等淮南故將如土芥,欲除之而后快!”
他猛地抬起头,双目赤红,言辞恳切,带著几分书生气的悲愤:“家叔耻与此等国贼同列朝堂!”
“今闻节帅提仁义之师,弔民伐罪,席捲江南,乃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
“故而,家叔愿效仿前朝英杰,弃暗投明,携江州一郡之地、黄册图籍、兵甲武库,尽数归於节帅麾下!”
“至於家叔本人……”
秦安的声音低了下去,透著一股万念俱灰的悲凉。
“自知身为降將,罪不容诛。”
“不敢奢求节帅宽宥,只愿以一死换取江州百姓安寧,换取麾下袍泽活命!”
“家叔已解下佩剑,只待节帅一声令下,便引颈自刎以谢天下!”
“自裁?”
刘靖把玩令箭的手指微微一顿,那双深邃如渊的眸子里,终於泛起了一丝波澜。
他没有立刻回答,而是缓缓站起身。
虽已夜深,但他甲冑未卸,显然时刻提防著城內的变故。
隨著他的动作甲叶摩擦,发出一阵细碎而悦耳的金属撞击声,在寂静的大帐中显得格外清晰。
刘靖绕过帅案,一步步走到秦安面前。
那沉重的皂靴踩在地面上的声音,每一步都像是踩在秦安的心口上。
“秦將军欲效仿田单復国,还是申包胥哭秦?”
刘靖突然问了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
秦安一愣,隨即明白过来,这是在考校他的心志。他连忙答道:“家叔不敢自比先贤,只求能如豫让一般,为知己者死,便死而无憾!”
“好一个『为知己者死』!”
刘靖抚掌大笑,笑声中充满了欣赏。
“本帅闻名久矣,恨未得见。”
“今日得將军之助,如鱼得水,如虎添翼!”
“何谈死字?”
他弯下腰,亲手將秦安扶起,语气诚挚无比:
“你回去告诉秦將军,徐温不识金玉,但本帅却深知將军之才!”
“似他这般百战余生的名將,乃是国家的柱石,岂可轻易言死?”
“本帅要他好好留著这有用之身,哪怕只是坐镇一方,看著这乱世终结,也胜过那毫无意义的愚忠赴死!”
说罢,刘靖右手探向腰间。
“仓啷——”
一声清越悠长的龙吟声,在大帐內骤然响起。
那声音带著几分金铁交鸣的杀伐之气,让帐內所有武將的目光都本能地匯聚了过来。
说罢,刘靖伸手探向腰间。
那里並非兵刃,而是一枚温润的羊脂白玉佩。
玉佩色泽通透,雕工古朴,乃是双鱼戏水的样式,虽不似兵符那般威严,却透著一股寧静致远的君子之气。
这是刘靖隨身多年的旧物,见证了他从微末走到如今的风雨。
刘靖解下玉佩,將其托在掌心,递到秦安面前。
“此玉,名为『双鱼』,乃本帅隨身之物。”
秦安跪在地上,看著那枚递到眼前的玉佩,浑身都在颤抖。
他当然知道这枚玉佩的分量。这不是权力的威压,而是一份无需言说的信任与接纳。
“节帅……这……这太贵重了!罪將万死不敢受!”
秦安的声音都在发飘,他下意识地想要后退。
“拿著!”
刘靖一声轻喝,不容置疑地將那枚带著体温的玉佩,塞进秦安颤抖的双手之中。
“告诉你家將军:古人云,君子温润如玉。本帅虽不敢自比古之贤君,却也懂得惜玉、护玉!”
刘靖俯下身,目光直视秦安的双眼,那眼神中没有杀气,只有千金一诺的诚意:
“只要他秦裴肯归降,本帅保他秦氏满门无恙!哪怕天塌下来,这枚玉佩,也替他挡著!”
这里没有封官许愿,没有这一刻就许诺的荣华富贵。
有的,只是一个“活下去”的铁券,和一个梟雄对另一个英雄的惺惺相惜。
秦安捧著那枚温润的玉佩,感受著玉面上尚存的温热体温,只觉得双臂有千斤之重。
在这乱世之中,这一句“保你满门无恙”,比什么万户侯都要来得实在,来得重!
秦安的喉头剧烈滚动,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大颗大颗地砸在那光洁的玉面上。
他唯有將头重重地磕在地上,用尽全身力气嘶吼出那个將会伴隨秦氏一门荣耀百年的承诺:
“节帅……主公大恩!秦氏一门,愿为主公效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待行完大礼,秦安缓缓起身,並未立刻离去。
他擦去脸上的泪痕,神色变得异常肃穆,对著刘靖再次深施一礼:
“主公厚爱,家叔无以为报。”
“家叔言,他身为败军之將,无顏苟活,更无顏面对主公的厚恩。故而,明日午时,家叔將在南门之外,行古礼赎罪!”
“古礼?”
一直沉默的袁袭轻捻须髯,眼中闪过一丝精光,似乎猜到了什么。
秦安点了点头,语气悲壮:“家叔说,他要让天下人知道,他秦裴降的不是势,而是义!他要用这身残躯,为主公铺平这进城的路!”
说罢,秦安再拜,捧玉转身离去,背影决绝而苍凉。
大帐內,再次陷入了沉寂。
柴根儿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大帅,啥叫古礼赎罪?这老儿明天到底想干啥?不会是想在城门口抹脖子吧?”
柴根儿挠了挠头,一脸茫然:“大帅,啥叫古礼赎罪?这老儿明天到底想干啥?不会是想在城门口抹脖子吧?”
话刚出口,他猛地打了个激灵,那一双铜铃大眼瞬间瞪得滚圆,仿佛想到了什么极其可怕的事情:
“不对!大帅,这不会是个套儿吧?”
“啥古礼不古礼的,俺听不懂!但他要是把咱们骗到城门口,说是要行礼,却突然杀出几千伏兵……”
柴根儿的声音陡然拔高,带著一丝难以掩饰的惊恐:“这说不定是诈降啊!”
刘靖没有回答,只是看著那空荡荡的帐帘,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弧度。
袁袭手中的书卷轻轻敲击著掌心,目光幽深。
“若在下所料不错,明日这场戏,怕是要震动整个江东了。”
“主公,这秦裴,是个聪明人,更是个狠人啊。”
“狠人好。”
刘靖坐回帅案,目光如炬。
“对自己不够狠,怎么在这个吃人的世道里活下去?我倒要看看,明日他能给我一个什么样的惊喜。”
……
这一夜,寧国军的大营里,瀰漫著一股肃杀的铁血之气。
这些跟隨刘靖南征北战的老卒们,深知在大战前每一分气力的宝贵。
除了巡逻甲士沉重的脚步声,便只有磨刀石与兵刃摩擦发出的单调声响,在这寂静的黎明前显得格外清晰。
五更刚过,伙夫营那边便准时升起了炊烟。
因为之前为了急行军拋弃了大量輜重,伙夫营里並没有架起那种足以煮粥的大铁锅。
只有几口简易的行军吊锅下燃著篝火,锅里翻滚著並不算清澈的热水。
对於这支刚刚结束长途奔袭的精锐之师来说,能有一口热水来泡开行囊里的乾粮,就已经足够奢侈了。
布袋解开,里面装的是炒得焦黄的米粒。
抓一把炒米扔进木碗,再浇上一勺滚烫的热水,“滋啦”一声轻响,米粒吸饱了水迅速膨胀,腾起一股诱人的焦香。
若是运气好,还能从怀里摸出一小块私藏的咸鱼干扔进去,那便是一顿足以让人羡慕的“珍饈”。
对於这支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精锐之师来说,无论接下来是受降还是死战,填饱肚子永远是第一位的。
营地里,一队队士卒围坐在篝火旁,沉默而有序地轮流取水。
他们大多脸庞黝黑,神情冷峻,或是脸上带著尚未完全癒合的刀疤。
士卒们手里捧著的傢伙什儿五花八门。
有的捧著磨得发亮的木碗,有的端著半边葫芦瓢,甚至有那性急的汉子,直接拧开了平日里盛水的粗竹筒。
蹲在营帐前,大口大口地吞咽著刚刚泡开的炒米。
而在那片狼吞虎咽的嘈杂声之外,营帐一角却显得格外安静。
篝火旁,一名队正模样的汉子正借著火光,细致地擦拭著手中的横刀。
“头儿。”
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士卒咽下最后一口,抹了抹嘴,压低声音问道。
“听说那个秦裴要投降?咱们不用真刀真枪地干了吧?”
队正头也不抬,依旧专注地擦拭著刀身,声音平淡得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降不降,那是大帅和秦裴的事。咱们的事,就是把刀磨快,把甲穿好。”
队正这话说得硬气,旁边一个正在啃炒米的老卒点了点头,含混不清地附和道。
“头儿说得在理。咱们大帅那是天上的星宿下凡,既然敢来受降,心里肯定有谱。咱们瞎操那份閒心干啥?”
“话是这么说,可这心里头……”
另一个年轻些的兵卒把碗里的最后一口汤喝乾,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嘟囔道:“那淮南佬可都不是省油的灯,以前咱们吃过的亏还少吗?”
这句话像是一块石头投进了死水里,让原本稍微安定的气氛再次波动起来。
之前没怎么开口的弓手突然抬起头,那双细长的眼睛里闪烁著一丝狡黠与不安。
他压低了声音,像是怕惊动了什么不乾净的东西:“就是,我也觉得悬。万一是诈降呢?”
“那帮淮南佬,心眼子多得很。牛尾儿大哥不就是……”
“诈降?”
队正手中的动作停住了。
他缓缓抬起头,环视了一圈周围的弟兄,嘴角勾起一抹森冷的笑意,露出一口白森森的牙齿。
“那更好。”
队正將横刀猛地归鞘。
“仓啷”一声脆响,在这黎明前的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
“咱们弟兄,什么时候怕过死仗?若是真降,那是他们识相,算他们祖坟冒青烟;若是敢诈降……”
队正站起身,拍了拍腰间沉甸甸的刀柄,眼中的杀意瞬间暴涨。
“那咱们就正好借著这个由头,把这帮背信弃义的杂碎剁成肉泥!”
“对!杀光这帮狗日的!”
周围的士卒们纷纷低吼出声。
“都给老子把眼睛擦亮了!”
队正压低声音,语气森然。
“大帅有令,不得扰民。”
“但若是那秦裴敢玩阴的,咱们手里的刀也不是吃素的!”
“到时候,谁也別留手!”
这就是寧国军的精锐。
他们有血性,更有军纪。
他们渴望用敌人的鲜血来洗刷曾经的耻辱,但也时刻牢记著那个年轻统帅立下的规矩。
明日正午时分,无论城门后面是什么,这支虎狼之师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要么接受臣服,要么赐予死亡。
除此之外,別无他选。
……
翌日正午,潯阳南门外。
天公不作美,阴云低垂,如同一块吸饱了墨汁的破棉絮,沉沉地压在城头。
凛冽的江风夹杂著细密的雨丝,像鞭子一样抽打著人的面颊,带来刺骨的寒意。
寧国军两万精锐,早已在此整肃列阵。
雨水打在冰冷的铁甲上,匯聚成细流滑落,滴入脚下的泥泞之中。
战马偶尔打出的响鼻声,和那面巨大的“刘”字帅旗在风中发出的猎猎爆响,在空旷的天地间迴荡。
这种死一般的寂静,比震天的喊杀声更让人感到窒息。
刘靖身披盔甲,外罩一袭猩红如血的战袍,骑在紫锥马上。
雨水顺著他兜鍪上的红缨滴落,滑过他坚毅如铁的面庞。
他像是一尊雕塑,静静地注视著那座紧闭的城门。
“轰隆隆——”
一阵令人牙酸的摩擦声突然响起,打破了这令人窒息的死寂。
所有人的呼吸都在这一刻停滯了。
那扇斑驳厚重、包著铁皮的巨大木门,在沉重的绞盘声中,缓缓向两侧敞开。
从那幽深黑暗的城门洞里走出来的,是一个人。
一个赤裸著上半身、枯瘦如柴的老人。
寒风呼啸,卷著冰冷的雨丝,无情地抽打在他那赤红色的皮肤上,仿佛要將他最后一丝体温也夺走。
他低垂著头,花白的头髮被雨水打湿,凌乱地贴在额前,显得狼狈不堪。
他的双手被粗糙的麻绳反绑在背后,绳子的另一端,牵著一只同样瑟瑟发抖、咩咩哀鸣的雪白活羊。
在他身后,数十名官员和两千余士卒,亦是脱去了象徵身份的官服与甲冑,赤膊、赤足,如同一群待宰的牲畜,沉默地踩著冰冷的泥水,一步步向著这边挪动。
这一幕,太过诡异,太过淒凉,也太过……震撼。
连江风似乎都屏住了呼吸,只有那面『刘』字大旗在头顶猎猎作响,发出的爆裂声如同催命的鼓点。
柴根儿那句还没骂出口的脏话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他怎么也没想到,那个被他视为洪水猛兽的秦裴,竟然会以这样一种极度卑微的方式出现在面前。
借著阴惨的天光,他看清了秦裴身上那令人触目惊心的景象。
那不仅仅是赤裸的肉体,那是一卷用刀与血写就的功勋录!
一道道狰狞的伤疤,如蜈蚣般盘踞在老人的前胸、后背、手臂上。
有的深可见骨,有的皮肉翻卷虽然癒合却依旧泛著紫红。
这每一道伤疤,都是他为淮南杨氏流过的血,都是他身为武將的功凭。
刘靖身侧,一直神色淡然的袁袭瞳孔猛地收缩。
他那双总是眯著的眼睛陡然睁大,死死盯著雨幕中的秦裴,脸上露出了罕见的震惊与敬意。
“主公……”
袁袭的声音低沉而急促,带著一丝难以掩饰的颤抖。
“快!快下马!”
刘靖目光在秦裴那赤裸的上身和身后的白羊之间一扫而过,脑海中电光石火般闪过“微子面缚”、“郑伯牵羊”的典故。
“古礼赎罪……原来如此。”
刘靖低声喃喃,嘴角勾起一抹意味深长的弧度。
然而身旁的袁袭似乎並未听到主公的自语,又或许是眼前那一幕太过震撼,让这位平日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变的閒云野鹤彻底失了態。
他猛地向前半步,指著雨幕中的老將,声音因极度的亢奋而有些发颤。
这位早年被隱世道人所救,在深山道观中阅尽三千道藏与前朝秘史的记室,此刻脑海中那些泛黄的古卷仿佛活了过来。
“这是古礼啊!这是大周流传至今的诸侯大礼!”
袁袭深吸一口气,语速极快。
“昔年周武王伐紂,微子启面缚衔璧、肉袒乞降,以保殷商宗庙;春秋时楚庄王围郑,郑襄公肉袒牵羊,迎接楚师,以身代国受过!”
“此乃『肉袒牵羊』之大礼!意为视己如羊,任凭宰割,只求保全一城百姓与宗庙社稷!”
袁袭转头看向刘靖,目光灼灼。
“秦裴此举,是在拿他一世的名节、拿他身为武將最后的尊严,来赌主公的仁德!”
“他这是把身家性命,连同这江州的气运,全都交到主公手里了!”
“主公,此等忠烈之士,即便各为其主,亦当受重礼相待!”
“若能收其心,何愁大事不成!”
刘靖闻言,神色瞬间变得肃穆无比。
他虽然不通那些仪轨的细枝末节,但他懂人心,更懂权谋之道。
秦裴这一跪,不仅仅是投降,更是一场豪赌。
他赌上了自己的尊焉,来换取刘靖的一个態度。
很显然,他昨日表现了诚意,今日秦裴便投桃报李,展现了更大的诚意。
此礼一出,秦裴就彻底绑在了他刘靖的战车上。
肉袒牵羊,这是把身为武將的最后一点遮羞布都撕了下来,献给了新主。
若是往后他敢反叛,哪怕是在这样一个吃人的世道,也绝无一家诸侯敢再收留这个行过古礼、却又背信弃义之人!
好一个秦裴,好一招置之死地而后生!
刘靖深吸一口气,眼中的欣赏再也掩饰不住。
“先生教我,当如何做?”
刘靖低声问道。
“解衣衣之,推食食之!”
袁袭字字鏗鏘。
“主公当亲解战袍披其身,以示不忍其寒,彰显仁君之风!”
“当场斩杀白羊,意为旧怨如羊,一笔勾销。”
“再命人烹之,与將军分食,则君臣之义定矣!”
刘靖微微頷首,眼中闪过一丝明悟。
下一刻,在將士震惊的目光中,那位威震江南的寧国军节度使,竟猛地翻身下马。
“大帅!不可!”
就在刘靖准备下马后,柴根儿猛地横跨一步,如同半截铁塔般死死挡在了身前。
他声音反而压得极低,像是由牙缝里挤出来的,带著一股令人心悸的颤音:“这兴许是诈降!不!这绝对是诈降!”
牛尾儿的惨烈,成了他这辈子都跨不过去的梦魘。
“大帅!您忘了牛尾儿是怎么死的吗?!”
柴根儿眼眶通红。
“只要那老狗手一挥,那就是万箭穿心啊!俺不能看著您去送死!”
刘靖没有回头,也没有多余的动作,只是伸出一只手,重重地按在了柴根儿颤抖的肩甲上。
那只手却稳如泰山,瞬间压住了柴根儿那即將爆发的狂躁。
“大帅……”
刘靖打断了他,目光越过柴根儿的肩膀,直视著那座沉默的城池,语气森然。
“我刘靖带出来的兵,没有怕死的,更没有被嚇死的。”
“牛尾儿的教训我没忘,但我也绝不会因为怕,就错失了一个收復江州的机会。”
他拍了拍柴根儿的肩膀,声音缓和了几分,却更具力量。
“把心放在肚子里。你的命金贵,我的命也金贵。”
“我还没带著你们打下天下,坐那凌烟阁,怎么捨得死在这儿?”
柴根儿浑身一震。
他深吸一口气,咬著牙,从喉咙深处挤出一个字:“诺!”
他侧身让开了道路,但並未归位,而是保持著一种隨时暴起发难的姿势。
那双充满血丝的眼睛,依旧死死锁定了城门的方向。
安抚住这头隨时可能暴走的猛兽后,刘靖深吸了一口气,迈出了第一步。
他的左手下意识地在那冰冷的刀鞘上摩挲了一下。
毕竟,把后背完全暴露给一座隨时可能射出万箭的城池,哪怕是赌,也是一场豪赌。
但他的脚步没有丝毫停顿,皂靴踏入泥泞之中,溅起一片泥水,毫不在意。
他不顾亲卫的阻拦,挥退了想要上前的持盾甲士,大步流星向著跪在雨水中的秦裴走去。
秦裴正跪在冰冷的泥水中,额头触地,浑身已被冻得发紫,牙关在不受控制地打颤。
他听到了脚步声,听到了那沉重的甲叶撞击声,但他不敢抬头。
心中却是一片惊涛骇浪。
他怎么下来了?
按理说,那刘靖应当高坐马上,受了自己这番大礼,再定生死。
如今这脚步声越来越近,难道是嫌自己这番做作太过碍眼,要亲手斩了自己?
恐惧几乎让他几乎窒息。
是一刀落下的人头滚滚?
还是极尽羞辱的嘲讽?
忽然,背上一暖。
一件带著体温的散发著淡淡龙脑香气的披风,温柔地覆盖在他那满是伤疤的后背上,隔绝了刺骨的寒风与冰雨。
秦裴身躯猛地一僵,他缓缓抬起头。
映入眼帘的是刘靖那张年轻而坚毅的脸庞。
那双眼睛里,没有胜利者的傲慢,没有对败军之將的鄙夷,只有满满的痛惜、敬重,还有一种让他心颤的……知己感。
“將军这是何苦!”
刘靖双手有力地握住秦裴冰冷的双臂,不容分说地將他扶起。
他的手掌温热而有力,仿佛透过肌肤,將力量传递给了这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將军镇守江州,保境安民,乃是忠臣良將!”
“那徐温不识金玉,是他有眼无珠!今日將军弃暗投明,不使这江州生灵涂炭,免去了一场浩劫,这才是真正的大仁大义!”
直到秦裴眼中的试探彻底融化,刘靖紧绷的后背才悄悄鬆弛下来。
他鬆开握著秦裴手臂的手,掌心已是一片滑腻的冷汗。
刘靖目光扫过秦裴胸前那道从左肩斜劈至右肋的狰狞刀疤,那是多年前秦裴为救杨行密而留下的旧伤。
刘靖深吸一口气,声音突然拔高,响彻三军。
“本帅常闻,前唐翼国公秦叔宝,阵前流血数斛,一生忠勇无双,乃天下武人之楷模。今日见秦將军这满身伤痕,方知古人诚不欺我!”
“这一身忠肝义胆,实乃秦氏家学渊源,一脉相承!”
“將军不愧为叔宝公之后!能得將军相助,是我刘靖之幸!是这江南百姓之幸!”
这番话一出,秦裴的心头猛地一颤,继而便是难以抑制的狂喜。
他当然明白刘靖这是在回应他准备的古礼,更是在给他乃至整个秦家一份天大的恩典。
这世道,谁不想给自己找个显赫的祖宗?
就像刘靖自詡汉室宗亲一样,那是为了正名分。
可他秦裴跟前唐翼国公秦琼八竿子打不著,若是他自己出去嚷嚷说是秦琼后人,只怕会被天下人嗤笑,骂他恬不知耻,乱认祖宗。
但这如果不从他嘴里说出来,而是从威震江南的寧国军节度使刘靖口中说出来,那分量就完全不一样了!
刘靖说是,那就是!
不是也是!
从此往后,他秦裴这一脉,就是堂堂正正的秦琼之后!
谁敢质疑?
要知道,秦琼秦叔宝的名声,不管是朝堂还是民间,那都是一等一的好,忠、勇、仁、义、孝全占了,简直可以堪比关羽。
认了这么一个祖宗,他秦裴家族往后的名声,那是镀了一层金身啊!
秦裴呆住了。
若说方才的“解衣推食”只是让他感到惊讶,那么此刻这番“正名之论”,则是彻底击穿了他作为武將最后的防线。
在这宦海沉浮半生,他早已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即便明知眼前这位年轻雄主此刻或许存了收买人心之意,是在做给天下人看。
可当他抬起头,迎上刘靖那双清澈如渊的眸子,看到那张丰神俊朗、隱隱透著龙虎之姿的面庞,他心中那道坚硬的防线,终究还是在这一刻土崩瓦解。
古人云:相由心生。
有著这般器宇轩昂之相,又能道出这般掷地有声之语,岂是池中之物?
恍惚间,秦裴仿佛看到了当年的吴王杨行密。
可即便是那位一手开创了淮南基业的雄主,在面对降將时,恐怕也难有这般毫无芥蒂的胸襟与气魄。
若是杨行密在此,或许会赏,或许会用,但绝不会像眼前这位一样,解衣推食,以国士待之!
便是演戏又如何?
能在这个吃人的乱世,给他这份体面,给他这份知遇之恩,这齣戏,他秦裴便愿意拿命去陪他唱到底!
泪水混合著雨水,顺著他苍老的脸颊肆意流淌。
那一刻,无数复杂的情绪如决堤的洪水般涌上心头,衝垮了他所有的克制。
委屈,半生戎马却被猜忌拋弃的委屈。
感动,被敌军主帅视若国士的感动。
震撼,被正名为“秦琼之后”的震撼……
种种情绪如洪流般衝垮了他的心堤。
士为知己者死,大概便是如此吧。
“主公……”
秦裴双膝一软,再次重重跪倒,这一次,不是礼节,而是五体投地,心悦诚服。
“罪將秦裴……愿为主公效死!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刘靖哈哈大笑,並未让他多跪,再次用力將他扶起。
隨后,他拔出腰间横刀,寒光一闪,那只系在秦裴手腕上的白羊应声而倒,血染泥泞。
“来人!”
刘靖收刀入鞘,豪迈挥手:“將此羊烹了!今日大摆筵席,本帅要与秦將军对席饮宴,啖肉佐酒!过往种种,皆如此羊,一笔勾销!”
雨,不知何时停了。
乌云散去,一缕金色的阳光穿透云层,洒在这一老一少两道身影之上,给那猩红的披风镀上了一层金边。
袁袭站在远处,看著这一幕,轻轻吐出一口浊气,眼中满是欣慰。
“风云际会,潜龙升渊……这江东的风云,今日算是彻底变了。”
这一幕,不仅震动了三军,更让一直缩在城门洞內、探头探脑观望的江州世家家主们心神巨震。
林家家主死死抓著城墙的砖缝,指甲几乎崩断。
他看著那个往日里威风凛凛的秦刺史此刻赤身跪在泥水中,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脚底板直衝脑门。
“狠人……都是狠人啊!”
他哆哆嗦嗦地擦了把冷汗,转头对身边同样面如土色的李家主说道:“秦裴这一跪,算是把咱们的路都给堵死了。”
“往后在这江州地界上,谁要是再敢对那位刘节帅有半点二心,都不用那位贵人动手,光是这一口『不义』的唾沫星子,就能把咱们淹死!”
“是啊……”
李家主看著远处那猩红的披风,眼中满是敬畏。
“不过也好,秦裴保住了命,咱们这几大家子的脑袋,也算是保住了。”
“快!传令回去!把那些藏在地窖里的金银细软都挖出来!”
“这个时候若是还藏著掖著,那就是不识抬举了!”
潯阳刺史府內,酒炙酣畅,宾主尽欢。
那只在城门口被斩杀的白羊,此刻已被烹成了香气四溢的羊汤,分发给了在座的每一位將领。
刘靖更是亲自为秦裴盛了一碗,这份殊荣,让江州的一眾降將彻底安了心。
酒宴上,秦裴敏锐地察觉到,那位一直站在刘靖身后、铁塔般的壮汉,看向自己的目光依旧充满了森冷的杀意。
他稍作打听,便知晓了缘由。
这位老將沉默片刻,忽然端起满满一碗酒,离席而起,径直走到柴根儿面前。
大厅內的喧譁声瞬间消失了,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
柴根儿握著骨朵的手指猛地收紧,青筋暴起。
秦裴却没有丝毫惧色。
他没有说什么场面上的虚言,只是指了指自己那苍老的脖颈,声音平静而坦荡。
“柴將军。老夫知道你在怕什么,也知道你在恨什么。”
“今日老夫降了,便是自家兄弟。但你若不信……”
秦裴上前一步,將那脆弱的脖颈暴露在柴根儿面前,距离那把骨朵只有半尺之遥。
“將军是忠义之人。若往后老夫有半点异心,无需大帅下令,將军这柄骨朵,便是老夫最好的归宿!”
说罢,秦裴仰头,將那一碗烈酒一饮而尽,將碗底亮给柴根儿看。
柴根儿愣住了。
他看著眼前这个坦荡的老头,看著他脖子上暴起的青筋和那道横贯喉结的旧伤疤。
那股一直憋在心里的邪火,仿佛被这一碗酒给浇灭了大半。
良久,柴根儿哼哧了一声,一把抓起桌上的酒罈子,仰脖猛灌了一大口,酒水顺著鬍鬚流淌。
“算你这老儿有种!”
柴根儿抹了一把嘴,瓮声瓮气地嘟囔道:“脑袋先寄著!俺帮你看著!”
刘靖坐在上首,看著这一幕,嘴角勾起一抹淡淡的笑意。
酒宴散去,夜色渐深。
刘靖並未休息,而是与秦裴对坐,案上摆著一张详尽的江州舆图。
“秦將军。”
刘靖指著舆图上的江州城,语气诚恳,没有半分酒后的醉意。
“將军镇守江州多年,威望素著,更深得军民之心。这江州若换了旁人来守,本帅还真不放心。”
他直视秦裴,正色道:“本帅欲任命將军为江州制置使,总领江州军政,继续镇守此地,操练新兵,为我寧国军守住这长江天险。不知將军意下如何?”
秦裴闻言,身躯微震。
他原以为,刘靖最多给他一个閒散高官,或是將他调往歙州安置,绝不敢让他继续在老巢掌兵。
这可是江州啊!
是扼守长江的咽喉,更是他秦裴经营多年的根基所在。
刘靖竟然如此大胆,敢重新交回他手中?
这份器度与魄力,令秦裴彻底折服。
他当即推金山倒玉柱,单膝跪地,抱拳喝道:“主公如此信重,末將……唯有肝脑涂地,以报天恩!江州在,秦裴在;秦裴在,江州必安如泰山!”
“只是……”
裴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难以掩饰的忧色,长身一揖。
“末將降主,罪在一人。但广陵城中,尚有拙荆与犬子……恐遭徐温老贼毒手。恳请主公……”
“將军放心。”
刘靖抬手虚扶,打断了他的话,神色平静地说道:“此事,本帅早已为你虑及。”
他从袖中取出一封早已写好的书信,递给秦裴。
“此信明日便会由专使送往广陵。信中,本帅会向徐温『借』回將军的家眷。”
秦裴接过信,心中依旧忐忑:“主公,徐温此人,心胸狭隘,睚眥必报。他未必会……”
“他会的。”
刘靖的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因为这封信,只是明面上的仪程。真正让他不得不放人的,是另外两样东西。”
刘靖伸出两根手指。
“其一,是这个。”
他从怀中取出一方丝帕,上面有几行清秀的字跡,落款处还有一个鲜红的指印。
“这是徐知誥的亲笔信。信中,他『恳请』义父以大局为重,莫要因私怨而伤了两家和气。”
徐温虽有六子,但这长子徐知训骄横跋扈,难堪大任;其余诸子亦多平庸。
唯有这养子徐知誥,恭谨孝顺,又深通谋略,实乃徐家在朝堂军中不可或缺的臂膀。
如今徐温虽大权独揽,然诛杀李遇之举已令朝野侧目,內有杨氏旧臣虎视眈眈,外有强敌环伺,正如烈火烹油,稍有不慎便会引火烧身。
若是再失了徐知誥,无异於自断一臂,更会让那些本就惊惧不安的淮南旧將彻底寒心。
这份轻重,以徐温的老辣,绝不会拎不清。
“其二……”
刘靖的眼神变得幽深。
“早在將军出降之前,我镇抚司的『田鼠』们,就已经在广陵城里活动了。”
“如今的广陵城,恐怕早已传遍了一个谣言——『江州秦裴之所以兵败,皆因监军徐知誥暗通刘靖,临阵倒戈』。”
秦裴闻言,倒吸一口凉气,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
好狠的手段!
这个谣言一旦传开,徐温为了自证清白,为了稳住军心,为了保住徐知誥这个养子的“忠名”,就必须做出样子。
如果他杀了秦裴的家眷,那岂不是坐实了“徐知誥投敌,徐温迁怒报復”的罪名?
所以,他不仅不能杀,反而要客客气气地把人送回来,以此向天下人昭示。
看,我徐温何等大度,徐知誥何等忠心,这都是刘靖的离间之计!
刘靖看著秦裴那震惊的表情,继续淡淡说道。
“徐温是梟雄,梟雄不计一时之失。一个徐知誥,其用处远胜过將军一家老小的性命。他会算这笔帐。”
“所以,將军只需在江州安心练兵。不出半月,尊夫人与令公子,必会安然抵达歙州。”
刘靖特意强调了“歙州”二字。
秦裴心中一凛,隨即释然。
家眷被接到歙州,名为安顿,实为人质。
这是帝王心术,理所当然。
但秦裴的心,却在这一刻猛地抽搐了一下。
他当然知道徐知誥的分量。
那是徐温的左膀右臂,是淮南的半壁江山!
握著这张王牌,本可以向徐温漫天要价,甚至可以换取几座城池、万两黄金!
可如今,为了他秦裴的一家老小,刘靖竟然毫不犹豫地把这张王牌给打了出去。
这是何等的恩遇?这是何等的重情重义?
秦裴的眼眶瞬间红了,他想要说些什么,却发现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千言万语都化作了一股滚烫的热流。
他颤抖著双膝,再一次重重跪下,额头死死抵在冰冷的青砖上,声音哽咽得几乎破碎。
“主公……以国士待我,秦裴……秦裴纵是万死,也难报主公大恩啊!”
这场千里之外的暗战,在刘靖轻描淡写的几句话中,便已布下了弥天大网。
刘靖没有急著说话,而是伸出双手,用力將这位老將扶起。
他轻轻拍了拍秦裴的后背,直到对方颤抖的肩膀慢慢平復下来。
“將军言重了。”
刘靖温言宽慰了几句,待秦裴情绪稍定,才缓缓转身,將目光移向舆图上那条奔流不息的大江,神色也隨之变得肃然起来。
“既然家事已定,那咱们就来说说这国事。”
“陆上本帅放心了,但这水上……还得问问將军。”
“原江州水师,现存几何?”
听到这个问题,秦裴脸上闪过一丝痛惜之色,嘆道。
“回主公,之前钓磯岛一战,可谓惨烈。末將的水师虽说是老底子,但也没占到便宜。五牙大战船仅余两艘,车轮战船也只剩下十八艘,能战之卒,不足千余人。”
刘靖微微頷首,並不意外。
钓磯岛之战,甘寧率领的新式水师虽然凭藉船坚炮利打得凶猛,但毕竟成军日短,论起水上接舷廝杀和操舟的歷练,確实不如江州这帮在水里泡了半辈子的老卒。
那一仗,说是两败俱伤也不为过。
“千军易得,一將难求。”
刘靖手指轻轻敲击著案几,若有所思地问道:“不知这水师將领是何人?能与甘寧打成平手,当非泛泛之辈。”
秦裴也是久经沙场的老將,一听这话,便明白了刘靖的招揽之意。
他立刻答道:“回主公,统领水师者名为常盛。”
“此人乃是末將多年的老部下,也是潯阳本地人,自小就在江里討生活。”
“他於水战一道极有天分,这十几年隨我南征北战,大小水战不下百余场,是个在江水中浸泡大的弄潮儿。”
“常盛……长胜,好名字!”
刘靖抚掌笑道:“既是良將,不可埋没。明日让他来见我。”
翌日清晨,江州刺史府后堂。
天色微亮,晨雾尚未散去,一名身形精瘦、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便已候在阶下。
他穿著一身半旧的皮甲,裤管高高捲起,露出满是伤疤和老茧的小腿。
那双脚赤著,脚掌宽大厚实,脚趾抓地极稳,仿佛隨时站在顛簸的甲板上一般。
眼睛不大,却透著一股如同鹰隼般的锐利。
此人正是常盛。
“末將常盛,拜见节帅!”
常盛声音洪亮,带著一股子江风的粗獷。
刘靖端坐於上首,手里捧著一卷水经注,並未急著叫起,而是上下打量了他一番,目光最终落在他那双赤脚上,嘴角微微上扬。
“常將军不穿靴?”
“回节帅,水上討生活,穿靴那是给淹死鬼预备的。赤著脚,心里踏实,脚底板能知水性。”
常盛回答得不卑不亢。
“好一个能知水性。”
刘靖放下书卷,神色一正:“本帅且问你,若要在鄱阳湖口设伏,以遏制顺流而下的楼船,当用何策?”
常盛眼中精光一闪,几乎是不假思索地答道:“楼船虽大,但转舵不灵。若在湖口设伏,当选枯水期,用小舟满载芦苇火油,趁夜色顺风放火,逼其搁浅。”
“再以蒙冲斗舰从侧翼凿穿,定可全歼!”
“若是逆风呢?”
刘靖追问。
“逆风则不可用火。当以铁索横江,暗置水底,待其船至,绞起铁索,阻其去路,再以强弩硬弓射之!”
两人一问一答,语速极快。
从长江水文到战船布阵,从火攻之术到水底暗桩,常盛对答如流,见解独到,甚至在几处细节上提出了比刘靖预想中更为狠辣的战术。
“好!”
刘靖猛地一拍案几,大讚一声:“常將军果然是水战奇才,秦裴並未虚言!”
他站起身,从案上拿起一枚早已准备好的令箭,郑重地递到常盛面前。
“传本帅军令,即日起,任命常盛为寧国军水师右都指挥使!负责收编江州水师残部,即刻招募新兵,並在潯阳督造新式战船。”
常盛闻言,那张被江风吹得紫黑的脸上露出了难以掩饰的激动。他双手颤抖著接过令箭,重重跪地:“末將……领命!定为节帅练出一支百战水师!”
常盛刚刚领命离去,他那沉稳有力的脚步声在空旷的廊道上渐行渐远。
晨曦透过雕花木窗,洒在青石地面上,映出一片斑驳的光影。
刘靖端坐於主位,手中端著一碗刚刚沏好的热茶,茶汤碧绿,热气氤氳。
他没有喝,只是用茶盖轻轻拨弄著浮在水面的茶叶,目光似乎落在那一沉一浮的嫩叶上,又似乎穿透了茶碗,望向了更远的地方。
堂下,袁袭静立不语。
他看著刘靖那副若有所思的模样,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
良久,刘靖才放下茶碗,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
“你以为,这常盛如何?”
刘靖的声音很平淡,像是在问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
袁袭放下书卷,不答反问:“主公是问其才,还是问其心?”
“哦?”
刘靖抬起眼,来了兴致。
“有何分別?”
“论才,此人久经水战,深諳长江水性,又对战船建造颇有心得,实乃不可多得的將才。主公破格提拔其为水师右都指挥使,可谓知人善任。”
袁袭顿了顿,话锋一转,眼中闪过一丝精光。
“但若论其心……此人乃秦裴旧部,在江州水师中根基深厚,一呼百应。”
“主公將新编水师交於其手,虽能迅速形成战力,却也如利刃在手,能伤人,亦能伤己。”
这番话,点到即止,却已將其中利害剖析分明。
刘靖闻言,非但没有忧虑,反而笑了起来。
“你之所言,正是我意。”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负手望著远处那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长江,声音悠远而沉稳:
“甘寧,乃是过江猛虎,勇则勇矣,却也野性难驯。”
“这些年,我寧国军水师从无到有,全赖他一人之力。这既是水师之幸,也是水师之患。”
“一军之內,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面旗帜,这是好事。”
“但若是这声音、这旗帜,只认甘寧,不认我刘靖,那便不是好事了。”
刘靖转过身,目光灼灼地看著袁袭。
“我需要一头蛟龙。一头同样能翻江倒海的蛟龙,把它投进这长江里,与那头猛虎斗上一斗。”
“只有让他们互相撕咬,互相忌惮,他们才会明白,这江水究竟有多深,也才会明白,谁才是这江水真正的主人。”
“我不需要他们亲密无间,我只需要他们都听我的话。谁听话,谁能打胜仗,谁就有肉吃,有官做。谁不听话……”
刘靖的声音骤然转冷。
“这长江里,多的是葬身鱼腹的枯骨。”
袁袭抚掌而笑,眼中满是讚赏。
“主公高明。”
他躬身一拜,语气中带著几分嘆服。
“猛虎在山,蛟龙在水,皆受主公驱策。如此一来,我寧国军水师方能真正如臂使指,无往而不利。”
刘靖重新坐下,端起那碗已经微凉的茶,一饮而尽。
“派系,从来都不是癥结所在。”
他放下茶碗,声音恢復了平静。
“癥结在於,坐在上面的人,能不能压得住。杨行密能压住,所以他创下了淮南基业;杨渥压不住,所以他死无葬身之地。”
刘靖顿了顿,目光变得有些幽深,望向了那个远在北方的庞然大物。
其实朱温那老贼也是一样。
如今他还活著,威震天下,麾下那些骄兵悍將自然无人敢动。
但他心里也明白,他那一窝儿子,没一个能像他一样镇得住场子。
所以他一建国,就开始举起屠刀,疯狂清理各派系的势力,想为子孙铺路。
只可惜,屠刀虽然快,却也寒了人心啊。
三日后,江州城內秩序尽復。
傍晚时分,夕阳如血,將滚滚长江染成了一片赤金。
刘靖摒退了所有扈从,只带著袁袭一人,登上了那座屹立於江畔、阅尽千帆的潯阳楼。
楼高百尺,江风猎猎,吹动著刘靖的玄色披风,发出如涛的声响。
他凭栏远眺,只见大江东去,浪涛汹涌,一艘艘渔船在金色的波光中如同螻蚁。
江的对岸,便是淮南的广袤土地,那里有他的下一个对手,徐温。
“你看这长江。”
刘靖的声音被风吹得有些飘忽,却带著一种与他年龄不符的沧桑。
“自古以来,多少英雄豪杰,欲饮马於此,北定中原;又有多少胡虏铁骑,望江兴嘆,折戟沉沙。”
“这江水,吞噬了多少王图霸业,又埋葬了多少枯骨亡魂。”
袁袭站在他身侧,目光同样望向那无尽的江流。
“江水东流,逝者如斯,诚然可嘆。”
袁袭的声音平静如初。
“但江水虽逝,两岸的磐石却万古不易。主公,便是那中流的砥柱,任凭浪涛冲刷,我自岿然不动。”
刘靖闻言,笑了。
他转过身,不再看那奔流的江水,而是看向自己年轻而有力的手掌。
那手掌上,有握刀留下的厚茧,也有批阅公文时沾染的墨痕。
“说得对。”
他缓缓握紧拳头,仿佛要將这万里江山都握在掌心。
“江水是留不住英雄的,因为它总是在流逝,总是在变老。”
刘靖抬起头,夕阳的余暉照亮了眼眸,里面燃烧著名为『雄图』的火焰。
他看著身边的袁袭,又想起了今日在堂下叩拜的秦裴,嘴角勾起一抹自信的微笑,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低声自语。
“但它带不走我。”
“因为,我才二十岁。”
江风依旧,吹不散那句年轻的誓言。
楼下的潯阳城,已是万家灯火,一个新的世道,正隨著这位年轻的雄主,悄然拉开序幕。
第362章 大周古礼
同类推荐:
我有一剑、
快穿之睡了反派以后、
全息游戏的情欲任务(H)、
四大名著成人版合集、
都市偷心龙抓手、
斗罗大陆III龙王传说、
傻小子,你大胆一点、
五零军婚,脚踹渣爹进城端铁饭碗、